数字史学为学者的工具箱提供了一个新的选项,至于这个工具是否称手,需要研究者不断返回历史语境,时刻观照历史研究的初心。让数字史学以一种“谦卑”的方式参与到历史知识的生成、传播与解释中,才能发挥其特有的效能。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飞速发展且丰富多彩的时代。历史学者不应仅仅作为旁观者去见证时代发展,更需要深入理解、研究时代,积极回应时代之问,不断推出具有思想穿透力的优秀成果。兑现这一学术承诺,必须在坚持科学理论指导的同时,寻求方法论的突破。作为一种方法论,数字史学的诞生与发展不断获得学界关注,它在特定研究领域中的突出优势,无疑呼应了百年大变局的时代需求,为推出优质、原创性研究成果提供了重要保障。
用数字史学呼应新时代需求
数字史学强调在历史研究中关注与运用信息技术,这不仅是历史学科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时代需要。实际上,回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越是主动回应社会现实、适应技术发展,越是能够提出优秀的研究问题。马克思感受到技术进步引发的工业革命,敏锐发现技术对产业工人带来的影响,开始了对资本、剩余价值、阶级等问题的思考,触发了《资本论》的创作。在大变革的时代,马克斯·韦伯认识到天主教徒群体与新教徒群体在社会财富、教育程度方面的差异,为他思考资本主义的起源提供了灵感。从上述两位学术巨人的学术路径来看,把握时代脉搏是学者的必修课,社会变革以及技术发展是学者产生问题意识的催化剂。
当前,信息技术已经深刻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技术引入历史研究,是历史学科发展不容忽视的趋势。如果认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久远过去的人与事,与现实社会存在一定的距离而对信息技术采取回避态度,就显得过于天真了。正如有学者指出,历史研究既需要面对“尘埃”(dust,指尘封的档案),也需要直面“字节”(byte,指电脑的信息存储单元),了解如何使用数字工具探索历史问题。数字技术不仅改变历史研究的过程,而且在图书馆、学术交流、课堂教学等多种场景中影响着历史学者的工作方式和状态。
当然,使用数字工具不单纯为了提升工作效率,更不是追赶时髦,而是意味着一种知识表示乃至知识生产的转型。早在1993年,就有学者在《连线》(Wired)杂志创刊词中预言知识存储方式将经历飞速发展的数字化进程,从而对传统的知识生产带来冲击。立足历史的长时段来看,数字化时代对人类社会知识生产的推动,甚至可以与人类掌握火的使用相提并论。
警惕技术万能主义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部分学者对数字技术的抵触情绪。他们不想被技术奴役,习惯在传统学术架构的舒适区怡然自得。但是,按照希契科克(Tim Hitchcock)的说法,人文学者要想“与数字技术对抗”,就必须认真对待数字技术。这种态度对于历史学者同样适用。对待技术的态度其实能够反映研究者的世界观,两种极端思想都不可取:视技术为洪水猛兽,可能会堕入狭隘主义的深渊,封闭研究视野;迷信技术万能,片面强调数字工具的“事实性”描述,则有简单化历史问题的嫌疑,可能得出贻笑大方的结论,犯上技术万能主义的幼稚病。这可能是一个类似“永恒九月”的议题,人们会时不时回到历史研究与技术关联的讨论路径上来,因为它确实存在讨论的价值。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计量史学兴衰的历史学者对待技术的态度,显然会同阅读科恩(Daniel J.Cohen)和罗森茨威格(Roy Rosenzweig)所著《数字史学》的同行有完全不一样的心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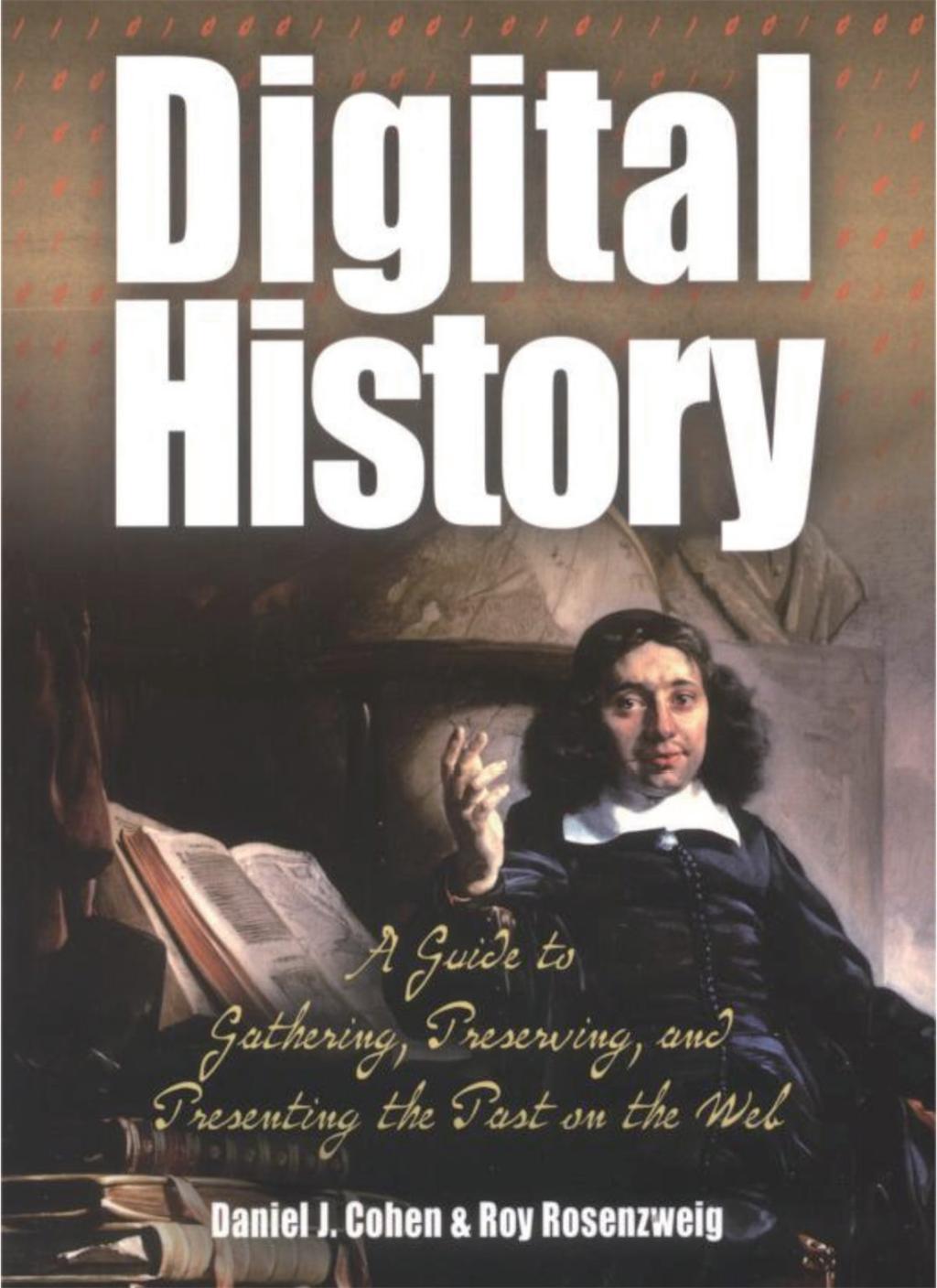
《数字史学》是第一本以“数字史学”为主题的学术专著,该书对数字史料的分析与整理,以及数字技术如何融入历史书写提出了独到见解。图为该书封面 资料图片
不过,在数字史学越来越受关注的当下,我们更加需要警惕技术万能主义的危害。把历史学科对客观性、科学性的追求,简单等同于对技术方法的迷恋,认为所有历史问题在技术的加持下能够迎刃而解,这样的做法实则拉低了历史学的品质。事实告诉我们,与已经实现了数字化生存的历史学者相比,历史事件与人物没有如此复杂的技术环境,其精神世界不可能超出物理世界的限度。当然,我们或许会惊异于意大利历史学者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在《奶酪与蛆虫》中描述的普通磨坊主形象,原本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多梅尼科·斯坎代拉,却拥有丰盈富足的精神世界,似乎超越了一位16世纪磨坊主应该有的知识范畴。但这个研究带给我们的冲击,更多源自研究视角从精英主义转向底层民众之后拓展出来的未知世界,而斯坎代拉的宇宙观仍然反映着宗教改革时期欧洲社会的文化潜流。因此,我们不能犯时代错位的常识错误,不能试图手握数字技术的宝剑去斩杀勃艮第的恶龙。学者邱伟云指出,数字史学擅长研究“巨观且复杂”的议题,因为相关问题涉及海量的材料而让传统研究方法望而却步。这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我们也需要在大量运用数字技术的研究实践中,克制技术万能的冲动,摆脱对数字化史料的依赖。加拿大学者伊安·米利根(Ian Milligan)观察到,原始史料的数字化完成度,深刻影响学者对研究议题的选择,从而导致研究方向、问题意识不协调的偏移,更会使史料的解读偏离历史真实。跳脱历史语境的技术型研究路径,可能会由于迷信工具理性而造成史学失去自己应有的品格。
数字史学仍需价值判断
有人会说,数字史学充分展示了技术维度的优势,一方面占尽全领域的结构化史料,另一方面基于算法获得硬核结论,因此有理由对相关研究的推进充满信心。对于出现与传统认知相抵触的结论,他们宁愿将其解读为学术“创新”。我们并非说研究结论不能与传统认知相悖,而是说历史有更复杂的问题需要观照,而且有更加需要关怀的历史语境。由于数字史学名声日隆,大量快餐式研究层出不穷,一些研究者用不同的文献套用数字分析工具的架构,做出大量性质雷同的研究,使史学成果退变为流水线上的工业品,而不是彰显研究者思想火花的成果,造成数字史学的虚假繁荣。这显然不是健康的学术生态。
造成这种虚假繁荣的原因,正在于研究者忽略了数字史学的价值立场。曾经,我们以为技术是中性的、科学是无国界的,但现实让我们看到立场无处不在。比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许多大语言模型也被运用到历史研究领域。语言模型虽然基于中性算法,但模型的训练依赖包含价值立场的数据集,从而影响到语言模型的立场。同理,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史料并非存在于真空中,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数字史学当然有助于我们更加高效地收集、整理史料,通过大量占有史料,使学术研究更接近于历史真实,但更为客观地解读史料,做出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研究,才是历史学的使命。在大家对“什么是数字史学”还存在争议的时候,我们不妨去反思“什么不是数字史学”,或许更容易参透玄机。那些用技术作为噱头的研究,无论其过程多么绚烂,如果没有贴近历史诉求,就难以称其为真正的数字史学。比如,仅仅由于19世纪出版的德意志报纸完成了数字化,便把文本挖掘、网络分析等典型的数字人文方法论套用到现成的数据库上,但并没有结合历史语境的分析,更没有立足时代背景的解读,这种“数字史学”研究很难具有学术价值,也无法获得生命力。
我们清楚地看到,即便数字史学让历史学者意识到工作环境已经从布满灰尘的档案室,转移到方寸之间的个人数字终端,变化程度不可谓不大,但数字史学研究仍继续受到研究者立场和视野的影响。与此同时,技术的运用并非总是意味着进步,也会带来系统的崩塌。正如互联网发明者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提到的那样,同样的担忧也存在于将技术引入历史研究的范畴之中:技术的垄断性,极端观点的出现,以及由于偏重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而倾向于接受片面信息,结果形成“信息茧房”等效应,都提醒我们需要有意识地避免落入技术的陷阱。从这个意义上进行反思,未加修饰的“数字史学”或许并非一个有效的术语。由于缺乏共同话语体系,学者尚未就“数字史学”的定义达成共识,而“数字”作为修饰的定语,会潜移默化地强调某些方面,但被强调的特质可能并非最核心的内容。更优的选择可能是使用一种描述性的话语,即“数字时代的历史研究”,反而能够更准确表达真实诉求——落脚点依然是“历史研究”,而“数字时代”则能够凸显在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研究工作。这个描述性的定义能够让史学工作者回望自己作为历史学者的初心,而不会被外在的技术手段所束缚。
我国数字人文领域的知名学者冯惠玲教授指出,技术与人文研究要获得实质性和有效性的连接,需要双方相互欣赏、相互借鉴,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协同发展,从而实现历史研究与数字技术的同频共振。在研究工作中,历史学家应当坚持自主性,把技术当作研究者的助理,而不能任由技术喧宾夺主,取代知识生产中的辨析、考证等创造性活动。所以,将技术嵌入历史研究,仍然需要体现出历史学科的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历史研究不能因为技术而放弃科学理论的指导,历史学家如果不假思索地在研究中套用语言模型工具,就可能在潜移默化中接受隐匿在模型中的价值立场,它可能与研究者信奉的原则相抵触。价值判断不仅是数字史学实践中不可缺省的内容,也是避免因技术应用滑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安全阀。
这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希腊哲学关于知识分子的职业伦理认知中,看轻思维开阔的狐狸,抬举关注独门绝技的刺猬,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传统的史学训练,就是在培养刺猬那样心无旁骛、具有专门技艺的史学工作者。但是,在当下的信息环境中,做深度研究还是开放性研究,似乎成了一个问题。不过,这并非要人为造就一个两难境地,我们希望将二者结合起来,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既有广博的知识,又能够深刻钻研,用数字史学提供的眼界与方法武装自己,不断升级为善于提问的研究者,在大变局的时代做一只充满想象力的“刺猬狐”。
总而言之,因应新时代的学术发展,史学工作者需要有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和心态,去尝试和接纳一切有利于研究历史和讲述中国故事的方法。从本质上看,数字史学为学者的工具箱提供了一个新的选项,至于这个工具是否称手,需要研究者不断返回历史语境,时刻观照历史研究的初心。让数字史学以一种“谦卑”的方式参与到历史知识的生成、传播与解释中,才能发挥其特有的效能。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原文载自:《历史评论》2023第2期
转载自:中国历史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